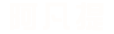我在上一家公司,事业上几乎一无所成,但在工作期间听了几个故事,或许算的上是我在这家公司值得回忆的不多几件事之一。
首先说其中一个主要的故事,一个科学家逆天改命的故事。这是我在这家公司的老板给我们说的故事。
我们老板——准确说前老板,1982年北大物理系毕业,然后留学美国,在纽约大学获得物理学博士。后来回国搞房地产,再后来成为我们这家互联网公司的老板。
这个故事就是这个老板说的。因为故事的主人公算是名人,后来我又查了一些资料。这样我的讲述就能比我们老板更完整一点。
英国数学家G.H.哈迪有句名言:“数学是年轻人的游戏,我不曾听说有任何重大的数学发现是由50岁以上的人做出的”。大概这个观点深受数学业内认可,相当数学领域诺贝尔奖的菲尔兹奖,就只奖励给40岁以下的年轻人,可能评奖者也认为超龄获奖的概率几可忽略(数学领域另有不限年龄的沃尔夫奖,但那个更象是终身成就奖)。
但有一位数学家,不仅接近60岁才发布载入数学史的重大成果,而且这位“老人”,只有大学讲师头衔,一度长期脱离数学研究工作,在58岁之前几乎没有任何有影响力的论文。
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叫张益唐,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数学系,被同学一致赞誉为数学天才,本科毕业后,1985年来到美国普渡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导师是来自台湾的华裔数学家莫宗坚。
张益唐攻读博士期间,用七年时间研究雅可比猜想,终于在博士论文中宣称证明了雅可比猜想。
由于这个猜想在数学界的影响力,各国数论学家群起查阅、审视张益唐的论文。结果发现论文中引用了莫宗坚的一个论文成果,进而又发现那个论文成果是错误的,张益唐的证明就此被推翻,论文也就无从发布,只是普渡大学认为张益唐的证明仍然有部分的可取之处,依然授予了张益唐博士学位。
但是,导师莫宗坚认为由于张益唐的牵连,自己的一项重要成果被否定,迁怒于张益唐,拒绝给张益唐写推荐信。
在美国,博士毕业后一般都能获得导师写推荐信,有的导师甚至会帮自己的学生去电话推荐。对于纯数学领域的博士生,拿到推荐信通常最差也能找个博士后的岗位。但因为莫宗坚拒绝写推荐信,所以没有哪个大学、研究所收张益唐。张益唐到处碰壁,无法找到与数学有关工作来谋生。
离开校园的张益唐四处流浪,在中餐馆打工,在汽车旅馆打工,有时无处安身就睡在汽车里,在北大同学那里蹭饭。后来他终于在快餐连锁店赛百味谋到个餐馆服务员的稳定工作,负责洗盘子、送外卖,偶尔兼个临时会计,用他的数学特长报税。这期间,张益唐认识了一个中餐馆的华人女服务员,展开追求并与她结婚。
张益唐在美国的北大同学,听说当年的数学天才老张沦落到餐馆当服务员,都唏嘘不已。其中一个同学唐朴祁在美国大计算机公司工作,在计算机网络研究中遇到的一个算法难题解决不了,试着找到在餐馆打工的张益唐,大约3周以后,张益唐居然给出了解决思路。
唐朴祁对张的数学能力印象深刻,后来见到在新罕布什尔大学任职的葛力明推荐了张益唐,在葛的帮助下,张益唐在新罕布什尔大学获得一个临时讲师的职位。这时候张益唐已经离开大学七年。
在美国,讲师作为教学职位,收入比起同资历教授(包括助理教授)差很多,教学任务却远比教授们重。科研上来说,几乎得不到任何支持。张益唐的职位,不是一个数学家理想的职位。
回到大学的张益唐,在此后十多年仅仅发表了一篇论文,没有引起任何波澜。由于错过了数学家出成果的黄金年龄,看来,张益唐要像大多数这个年纪的人一样,平淡地过完自己的余生。
2013年的一天,58岁的张益唐,突然神秘兮兮地对自己老婆说:“留意媒体和报纸,你可能看到我的名字”。老婆对他说“你喝多了吧?”
2013年4月17日,没有告诉任何人,张益唐将论文《素数间的有界距离》投给世界数学界最负声誉的《数学年刊》。
张益唐的论文,开启了数学史最重要也是最难的猜想之一孪生素数猜想证明的里程碑的一步。
孪生素数就是指相差2的素数对,例如3和5,5和7,11和13…。孪生素数猜想提出:自然数k=1,存在无穷多个素数对(p,p+2k)。150多年来,数学家对于证明这个猜想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而张益唐的论文,则证明了自然数k=7000万,存在无穷多个素数对(p,p+2k)。
k从7000万到2,似乎距离证明还非常遥远,但在出现张益唐的成果之前,k相当无穷大,相比无穷大到7000万,7000万到2的距离就微不足道了。
更重要的是,张益唐开启了最重要的一步证明,按照这个基础,证明能够迅速的推进,张益唐的论文在5月14号面世,两个星期后的5月28号,k下降到了6000万,仅仅过了两天的5月31号,下降到了4200万,6月2号,则是1300万,6月5号,40万,2014年2月,缩小到246。
《数学年刊》的编辑将张益唐的论文发给罗格斯大学的亨里克·伊万尼克教授审阅,伊万尼克刚开始没太当回事,准备先把它放一放,毕竟张益唐是无名小卒。不巧,伊万尼克的朋友多伦多大学的约翰·弗里德兰德教授,打电话说自己也收到张益唐的论文,表示想和伊万尼克一起探讨一下.......
几周后,伊万尼克和弗里德兰德给编辑回信,“论文的主要结论是一流的。作者成功的证明了素数分布领域的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定理。虽然我们巨细无遗地研究了这篇论文,我们没有找到任何瑕疵……我们强烈建议‘数学年刊’接受这篇论文。”
论文发表后,很快就引起了数学界的极大关注,《自然》杂志、《》等众多媒体都进行了专文报道,张益唐顿时声名鹊起成为数学界的巨星。2014年8月,在四年一度的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张益唐获邀在闭幕式之前作一小时专题报告,这对一个数学家来说,堪称无比罕见的殊荣。
这位年近六旬,长期离开研究岗位,在不太知名的大学中担任临时讲师的人,几乎没有发表过专业论文的人,却为破解数学领域最著名猜想之“孪生素数猜想”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成为举世闻名的数学家。
我前老板给我讲的张益唐的故事说完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要给我们说这个故事,也许因为他们同是1978年入读北大的校友,也许他想鼓励我们刻苦攻关、努力研发。
我的文章写到这里,有的是逆天改命、逆流而上的励志人生。但这不是我这篇文章的全部,或者说这只是我想表达的第一个层面。
老板说这个故事的时候,充满了对张益唐的钦佩。他告诉我们,走科学研究这条道路,是非常艰难的,即使具备惊人的天赋,投入常人无法忍受的努力,往往也只能取得一点点成果——放在整个科学史,那点成果几乎无关痛痒。
就拿老板自己来说,他读博期间在国际比较知名的物理学刊物发表过三四篇论文,而能做到这点并不多见。他能够做到,不是因为他多厉害,而是他当时发现了一个算法的小小改进方向,然后抓住这个点不断写论文。发现这个改进大部分靠灵感和运气,用完这次运气,他就觉得再想取得成果真是太难了。必须耐得住寂寞,而且动辄就需要寂寞十年、二十年。
我的这个前老板,当年是以全省理科第4名考取北大物理系。他说,即使以北大的人才荟萃,他整届同学能在物理科研方面取得些许成就的,也屈指可数。
他以自己曾经最被人看好的一个同学为例:那个同学智商和情商都高得惊人。在北大读书时,其他同学总是拿着难题向他请教。后来他也去美国留学,很快就成为当地华人学术界兼社交界的风云人物。
“但是,”老板说,“我的这个同学已经不在了。很多年前,他就因为抑郁症自杀了。”
那么聪明的人为什么会得抑郁症?也许是科研压力,也许是聪明总伴随敏感和痛苦。对此我不确定。
在这个公司,我还认识了一个约60岁、姓吕的先生。他在公司任高级顾问,亲切随和、认真敬业,我们都称他为“吕老师”。
吕老师和我一样,都是江西南昌人,吕老师和我老板一样,都是海归。他也在80年代初考取公派留美,和老板一起在纽约大学读物理,俩人因此相识。
不同的是,他似乎对学术的专注似乎比老板还差。他生活的相当一部分工夫,都花在追女生方面,用现在带点负面的词就是爱“泡妞”。
早在准备留学考试时,他就在考前培训班追过一位自视甚高的女生——她年纪在那届留学生最小,成绩却出类拔萃,她对吕老师说:“我要找的男人,要比我聪明。你行吗?”吕老师涎着脸皮回答“我就是这样的男人”。
俩人相处过一段时间。多年以后,吕老师向我们回忆:“那时我的想法:出国以后再找女朋友可不容易。”
在纽约大学攻读物理硕士,已经到了毕业设计阶段,吕老师却忽然决定转到哈佛大学重新读生物学研究生。
那时候,他时常和一群哥们去哈佛大学玩,认识了一位生物系华人女生,惊为天人,全力展开追求,为了方便追求,不惜放弃快要到手的物理学硕士学位,跑到哈佛读生物学研究生。
他追的那个哈佛女生不仅漂亮,而且极其聪明,在哈佛也是一个学霸级的人物,心气很高,一心想做出惊世的科研成果。
吕老师说那个女生心思都在科研上,对恋爱不很投入,他也没花太多时间追求。因为同专业,两个人有机会常在一起。后来,就真在一起了。
女生拿到博士学位后,年纪轻轻拿到大学教职,再成为教授。总之,一切很顺利,俨然人生赢家。
可是,有段时间女生总闷闷不乐、心思重重,一副烦恼甚至痛苦的样子。吕老师就问什么事,女生刚开始不答。久了,长叹一声,对吕老师说:
吕老师是和我一边在公司食堂吃饭,一边回忆这段往事。我大吃一惊,我从来没有想到,世上竟然会有人为拿不到诺贝尔奖而感到痛苦、幻灭。
当年的吕老师也吓了一跳:我专业上可没什么野心,读生物就为了泡你。你这让我亚历山大的。
吕老师没有和那个女生走到最后,是不是和他压力大有关系?他没说,我就不知道了。
聪明、能干的人,往往心气高、责任重、目标远,当目标、责任超出了自己的能力,就容易带来痛苦。而有些人认清自己能力边界,沉浸于相对简单、容易的世俗快乐,反而更少痛苦。
吕老师就属于后者。也许是早早认识到自己不是搞科研的料,他拿到哈佛硕士后没有继续修读,而是去了一家公司担任了生物医药行业的分析员。多年以后再回到国内,在互联网公司工作。
吕老师在美国后来又找了一位女友,这次修成正果,她成为他妻子。俩人一起回国。或许吕老师就爱超级学霸,他妻子也是一位科学家,被国内“千人计划”引进,年龄比吕老师小20多岁。
不过按照我老板的说法:吕老师妻子这么受国内重视,不是因为有多惊人的成就,而是她掌握了一种特别的实验技术或者说工具。具体是什么?我不懂物理自然不知道。
我们这些同事包括老板,都有点好奇吕老师怎么能追到现在的妻子。吕老师虽然是情场老手,但并不滑头,是一个性格温和,待人也比较诚恳的人。我们只能猜想:也许女科学家的生活、工作都比较单调,难得有这样的男士表达爱慕和关心,因此被打动吧。
我那个老板当着吕老师面,多次表示没拿到物理学位就转学对吕老师是一件人生憾事。但“子非鱼安知鱼之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谁能说吕老师的人生不是丰富多彩呢?
我的故事到这里就全部说完了。我的故事提到一个人的励志人生,但这不是全部,我真正想说的是各种人生。
人生充满艰难险阻,像张益唐那样不惧艰难、勇于坚持,最终登上科研的顶峰,成为人生舞台的主角,无疑令人赞叹和敬佩。
但主角毕竟很少,更多的人只是配角,演好自己的配角同样很有意义。况且,主角和配角是相对的,可能你眼中的所谓主角,比如某个名牌大学的教授,在他所在的那个舞台其实还是配角。
也有一些人,早早发现角色不适合自己,选择更换自己的角色,比如我的前老板,就是这样。
另外,还有像吕老师这样的人,出演什么角色对他们来说似乎没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一种人生体验、一个过程,他们是生活角色的“体验派”(表演方法分体验派、方法派、表现派)。体验与人生舞台不同角色的交往、接触,有时比自我的成功更有意义。
对于人的个体来说,很难说哪种人生就没有价值,没有意义,它们共同构成了大千世界的缤纷色彩。
正如我在上上篇的文章中,引用了约翰·麦克马雷说的一句话:“我们的存在除了意味着充分地、彻底地成为我们自己以外,还可能有什么别的意义?”
版权声明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百度立场。
本文系作者授权百度百家发表,未经许可,不得转载。